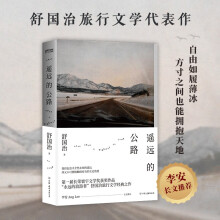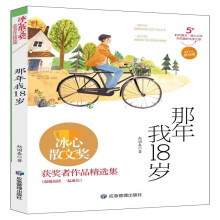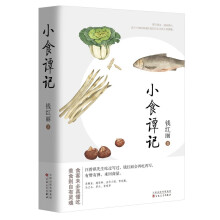透骨草
我像忘记那一场伤病一样忘记了透骨草。在很多时候,它更像是某件被我曾经反复用过的家什,渐渐地,使用的次数少了,或者是不再用了,却依然不忍心丢弃,便随手搁进生活的某个犄角旮旯里,转眼却忘记了。总是需要有某一个契机,才能引导我再次想起它们。
恰巧我的父亲记性非常好,每年进入伏天,父亲从山间归来时,手里总是会捏一把透骨草,然后将之随手插进粮房的椽隙里,任其慢慢阴干。阴干后的透骨草,依然保持着绿的色泽,等透骨草彻底干透了,父亲又小心翼翼地取下,剪掉毛根,装进白色的帆布袋里,写下名称,吊在椽上,以备急用。
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些备在家里的透骨草是没有用处的,父亲却总是不厌其烦地这样做,我没有阻拦过父亲,就依照着他的经验,把春天的茵陈蒿,夏天的蒲公英和透骨草带回家。
茵陈蒿、透骨草、蒲公英、杏核、杏干等等,父亲都会用帆布袋分类装上,然后吊在粮房的椽上,大大小小的帆布口袋吊在空中,像是吊了满屋顶形色各异的葫芦,任其慢慢地积满灰尘。待到来年,父亲依然会从山上带回各种草,等阴干了,把旧草掏出来,再把新的草又装进去,挂上,然后使其再落上一年的灰尘。
在我出生的乡间,透骨草算不得珍贵药草,它和茵陈蒿、蒲公英等野生的草一样,凡是在生长杂草的土地上,都能找到两三株透骨草来。而一年的伏天,就那么一小段时间,父亲说过,伏天的透骨草是一年中最好的药草,经父亲这么一说,透骨草就显得珍贵起来了。
父亲有备无患是对的。
我不慎扭伤了脚脖子,肿得很厉害,疼痛难忍。父亲摸摸我的脚,转身去粮房里取下帆布袋,拂去尘土,解开绳索,取出透骨草、蒲公英,从灶台上取来花椒,再搜出被母亲塞进墙缝里的乱发,放进砂锅,添上水,搁在火上熬成药汁,每日三次用之给我擦洗,不出七日,竟痊愈了。
那时,村上的药房里缺药,我家里缺钱,父亲索性就没有找大夫,照着他曾经给自己医治伤病的经验,亲自动手把我的伤病治好了。幸运的是没有留下任何病根,等伤病好了以后我问父亲,他怎么就有把握将我的伤病治好。父亲没有回答我,一声叹息,一丝苦笑,便是作答。
山间的草木,千姿百态,我的父亲并不懂得所有草木的功用,他只是粗浅地识得几味有用的药草,在空闲的时候,他就指着吊在屋顶上的那些帆布袋一一对我讲:透骨草,味辛,性温,热敷用于活血止痛,腰腿扭伤;茵陈蒿,昧苦、辛,清湿热,退黄疸,口服对治疗黄疸型肝炎有效;蒲公英,苦、甘、寒,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用于疔疮肿毒等。
关于透骨草,我只记得那次与伤病有关的一些情节,我只熟识那些被父亲不厌其烦地阴干的草,它们在很多时候就像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杂物,被父亲吊在粮房的屋顶上,成为粮房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它们仿佛只是用来被蒙上尘土,毫无用处。
我已经离开出生的那片土地多年,一些事物已然在我的心里变得模糊,我像忘记那一场伤病一样淡忘了透骨草。事实上,被我淡忘了的,何止只是透骨草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