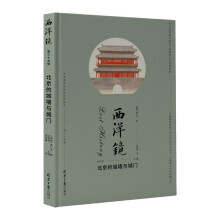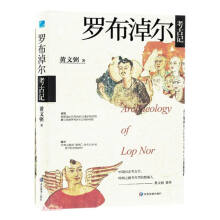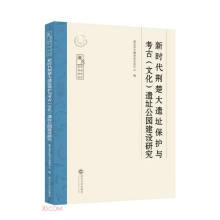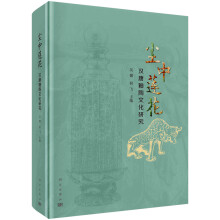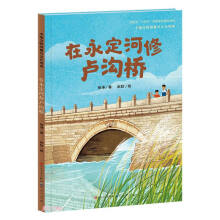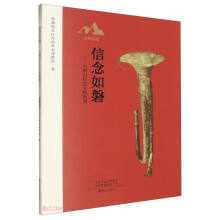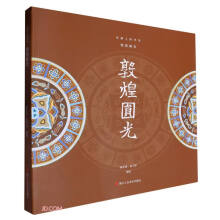**章 绪论
动物考古学是研究古代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科学,通过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等进行科学和系统的采集,开展鉴定、观察、测量、测试及各种统计分析,结合考古学的文化背景进行探讨,认识古代动物的种类、古代的自然环境和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代人类的行为,从特定角度来研究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探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1)。
从现有的学科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动物考古研究的时间范围多集中于先秦时期(此处的先秦时期指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2),对于历史时期(秦汉以后)的研究比较少且多集中于汉代墓葬出土动物研究方面(3),关于明代的动物考古研究就更少了。而从动物遗存的出土背景来看,以往的研究均以日常生活区和墓葬中出土动物为研究对象,很少涉及园林遗址中的动物遗存。因此,对于成都东华门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既是对西南地区动物考古研究资料的补充,也是对明清时期动物考古研究资料的补充,更是大型园林遗址动物考古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节 明代蜀王府的历史背景与建置沿革
明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朱元璋深感“天下之大,必建藩屏”(4),始立封建诸王制度。*代蜀王朱椿,系太祖朱元璋第十一皇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受封,洪武十八年(1385年)驻中都凤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就藩成都府。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正式下达了在成都修建蜀王宫殿的诏令,“敕谕四川都指挥使司及成都护卫指挥使司 蜀王宫殿俟云南师还,乃可兴工,以蜀先主旧城水绕处为外垣,中筑王城,敕至,徐图之,勿亟也”。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诏谕景川侯曹震“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仪”。洪武十九年(1386年),“赐蜀府营造军士万七千九百六十人,米八千九百七十九石,盐八万九千七百斤,钞各一锭”。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赐蜀府营造工匠钞,人各十锭,有死亡者给其家”。因其工程量太过浩大,对四川地方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曹震上疏言道:“四川之民,自国初创置贵州、黄平、松茂等卫,营造蜀府,征讨云南,禄肇诸处,积年劳役,请从末减。”后出于稳定西南统治的考虑,明太祖不得不答应减免赋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王府竣工,“蜀王府城垣宫室成,成都中护卫具图以进”。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蜀王府先后生活过的蜀藩王共计十世十三王。
终明一代,蜀王府在使用过程中尤其是明代中晚期,虽曾出现火灾、宫墙颓坏等多次不同程度的损毁,如嘉靖十七年(1538年),“蜀王府第火,奏乞重修,许之”;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蜀(成)王让栩以本府城垣顽坏,欲自备物料请给工匠修理,诏下抚按官勘明,量给工价助之”;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东府尽焚,至是门殿皆毁”;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蜀世子府灾”(;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蜀王府承运殿灾”(;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蜀府殿庭灾毁”(,但总体尚未遭受根本性破坏。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攻占成都,末代蜀王朱至澍投井自尽。张氏一度据蜀王府为宫,建立大西政权,改元大顺,并将原来的藩府正殿——承运殿改建为承天殿,府门外廊改建为朝房,作为新朝处理政务的场所。当年冬至,张献忠大宴百官,“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于“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表明此时的蜀王府经过政权易手后,依然恢宏堂皇,旧貌犹存。
清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大西政权在四川的局势已岌岌可危,即将撤离成都的张献忠竟然下令将王宫焚毁,明末及清代的大量史料或由作者亲身所历,或根据前辈传言,都证实了蜀王府及其宫苑建筑在这场旷世劫难中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例如,《明史 张献忠传》载“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1);法人古洛东(Fran.ois Marie Joseph Gourdon)《圣教入川记》是据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所著《张献忠传》(Rela 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ang-hien chungo famoso ladr.o da China,em e anno 1651)而成,保存了大西政权在川活动的**手资料,其书亦载“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2);沈荀蔚《蜀难叙略》谓“贼自出屯以后,日惟焚毁城内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观,火连夜不绝。惟蜀府数殿,累日不能焚,后以诸发火具充实之,乃就烬。其宫墙甚坚,欲坏之,工力与砌筑等,不能待而止”(3);彭遵泗《蜀碧》又云“贼毁藩府 又尽毁宫殿,坠砌堙井,焚市肆而逃。时府殿下有盘龙石柱二,亦名擎天柱。贼行,取纱罗等物杂裹数十层,以油侵之,三日后举火,烈焰冲天,竟一昼夜而柱枯折”(4);费密在《荒书》中则称:“焚蜀王宫室并未尽之物,凡石柱庭栏皆毁,大不能毁者则聚火烧裂之。成都一空,悉成焦土。”(5)清初人士吕潜夫面对蜀王故宫遗迹,追忆蜀府往事,不胜唏嘘:“边徼锡封怜少子,蜀王台殿*崔嵬。谁从辇路鸣鞭过,犹记宫门拜刺来”(6),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荒芜凄惨之状。另一位清代诗人葛峻起在《过明蜀王故宫》中写道:“宫墙遗址郁嵯峨,回*风烟感逝波 参差碧瓦留残照,寂寞荒榛带女萝”(7),亦是对蜀王府逝去辉煌的一丝哀叹。
自顺治三年(1646年)成都全城被焚毁后,省治暂设保宁(阆中),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由川陕总督李国英、四川巡抚高民瞻等人迁回成都,葺城楼以作官署。康熙四年(1665年),四川巡抚张刘格(后改名张德地)向清廷建议,在明蜀王府宫城旧址上改建贡院,并题写贡院门额,这就是后来清代四川贡院的来历(8)。
第二节 东华门明代蜀王府遗址的发掘概况与建筑性质
蜀王府位于成都旧城中部的武担山之阳(南),一改过去历代成都城市轴线北偏东30°的斜向布局,*次确立了正南北的中轴线。平面呈纵向的回字形,双重城垣,分为内城和外城两个部分。外城的城垣又称萧墙,东起今顺城大街,西至今东城根上街,北抵今羊市街和西玉龙街,南至今西御街和东御街,萧墙内分布山川社稷坛、旗纛庙、宗庙、驾阁库、典宝所、典膳所、典服所、良医所、承奉司、义学等机构,萧墙外南设金水河,东西向穿流而过,“(河面)并设三桥,桥洞各三,桥之南设石狮、石表柱各二”。内城又称宫城,宫墙东起今东华门街,西至今西华门街,北抵今东御河沿街和西御河沿街,南至今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周围五里,高三丈五尺,外设四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城垣外设御河环绕一周。宫城的中轴线设三大殿,由南往北分别为承运殿、圜殿、存心殿,两侧配置东府、西府、斋寝、凉殿、纪善所、广备库等设施,存心殿后为王宫门和王室寝宫。
2013~2019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成都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的建设,在东华门街一带连续开展了多年的城市考古工作,清理揭露出大面积的明代蜀王府建筑群。该组建筑群位于蜀王府的宫城东北部,东临宫城东墙,西临宫城次级干道,由水道、月台、踏道、拱桥、木构建筑、水池、台榭、码头等多类设施组成,占地范围南北长约240、东西宽约100米,总面积超过24000平方米。它们在平面布局、形制与构筑方式、出土遗物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因此具有相同的功能和性质。其中,水道G4和水池C4是该组建筑群的主体,水道G4分作东、南两段,相接处呈直角,平面近“L”形,南段全长85.3、宽10.3~12.7、残深3.5米,保存临水月台2座、拱桥1座(仅存南、北桥墩)、踏道3处;东段的大部分叠压于现代建筑之下,未揭露完整,残长22.3、宽8、残深3.5米,保存木构建筑1座。水道的修筑方式是先在地表开挖长条土圹,底部直接下挖至砂石层形成河床面。土圹剖面呈口大底小的倒梯形,圹壁砌筑长方形青砖,以石灰勾缝,青砖外垒筑红砂石条作为护堤。石条接触水体一面经过细凿加工,表面较平整,局部刻有“左”“右”等字,以“右”字居多。
水池C4平面似回字形,池体东西长44.5、南北宽39.8、残深2.4米,中部为台榭,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27.4、南北宽22.8、残高2米,台榭四周环以水道,宽8.1米,底部河床为砂石面。台榭南侧中部的堡坎有一长6.4、进深1.4、残高0.5米的凸出部分,残存阶梯式的踩踏面,可能为步道或码头之类的设施,用以停泊小船或人员上下。
从建筑群的构成要素看,如水道、水池、台榭、拱桥、码头等,多带有明显的水体景观性质,休闲游赏的功能显得十分突出。明《嘉靖四川总志》曾提到“诸葛祠在蜀府右花园西”,并且早在20世纪50年代,成都西郊发掘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明蜀中贵丁公墓”,据志文载,墓主人丁祥幼年进入蜀府担任宦官,先后侍奉蜀惠王、蜀昭王、蜀成王三代,“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并且在蜀昭王在位期间(1494~1508年),“擢于迎晖附郭左花园,经理四时进贡朝廷水土方物,制备庶品御需之类”。综合考虑,这组建筑群在性质上,应属于具有水体或园林景观功能的宫苑单元,并且以王府中轴线道路为参照物,采取了东(左)、西(右)对称的布局模式,很可能即与文献所载之“左(右)花园”。另外,这一区域还时常被冠以“内园”或“内苑”之名,出现在多位蜀王的个人文集中,如蜀定王文集——《定园睿制集 冬晴》“云散天开曙色晴,内园风景悦人情”,《定园睿制集 尝新樱桃次杜甫韵》“内苑樱桃颗颗红,中官初蔫满纱笼”;蜀成王文集——《长春竞辰稿 长春苑记》“形胜佳丽,内苑之地也”,《长春竞辰余稿 齐天乐 夜景即事》“内苑揽胜,楼中试看沉醉倒”。
蜀府为西南巨藩,素为明廷中央所倚重,新建蜀王府时,太祖朱元璋曾诏谕景川侯曹震“非壮丽无以示威仪”,其财力亦十分雄厚,明人陆釴《病逸漫记》言:“天下王府,惟蜀府*富,楚、秦次之。”张瀚《松窗梦语》亦云:“(蜀王)富厚甲于诸王,以一省税银皆供蜀府,不输天储也。”在此背景下,蜀王府之内修建规模宏大的宫苑园林区,自当是合乎常理的。
第三节 关于明代蜀王府动物资源的史料信息
关于蜀王府内部的动物资源,在明代四川地方文献尤其是各代蜀王的诗词、散文、笔记里,有着十分丰富的记载,兹按动物种类分别罗列如下。
1.乌鸦
《定园睿制集 月夜乌》:“君不见慈乌 忽闻枝上啼 禽乌尚知孝 人类反不如”《定园睿制集 围炉小酌》:“酒酣一*阳春调,不觉琼林噪暮鸦”;《定园睿制集 鸦》:“成群结阵过空城,风外横斜噪晚晴”;《定园睿制集 啼乌》:“万年枝上噪寒鸦 乌鸦啼在夜深时”;《怀园睿制集 栖鸦》:“倦飞归宿在高林,梦稳身安月有阴”;《惠园睿制集 灵乌》:“灵乌复灵乌,栖息托佳树”;《惠园睿制集 东白轩》:“乌鸟惊飞鸡振羽,一观天下喜开晴”;《惠园睿制集 朝回清兴》:“龙旗影动阳乌出,宝殿光浮冻雪消”;《长春竞辰稿 井》:“城鸦睥睨集,时听辘轳声”;《长春竞辰稿 舟中》:“远树归鸦集,维舟近晚凉”;《长春竞辰稿 仲春晚眺克慎轩前树构鹊巢偶作》:“渐看将暝色,数点宿鸦归”;《长春竞辰稿 锦城落日斜》:“鸦阵归林早,虫声倚砌吟”;《长春竞辰稿 密雾隔朝阳》:“鸦乱东隅白”;《长春竞辰稿 空山湿翠衣》:“鸦噪仍停树”;《长春竞辰稿 秋塘清兴十绝》:“暮鸦喧作阵,错落乱交翰”;《长春竞辰稿 杂兴十*》:“落日乱鸦归”;《长春竞辰稿 枯木寒鸦》:“垒石巉岩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