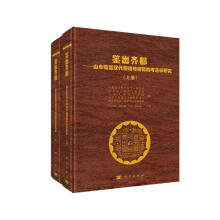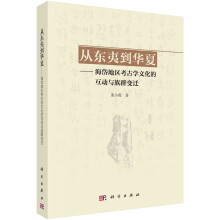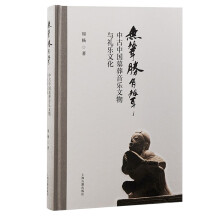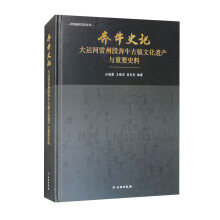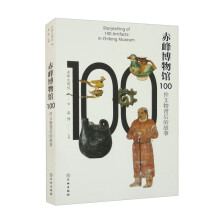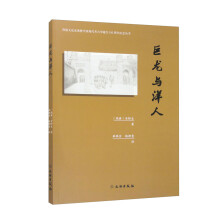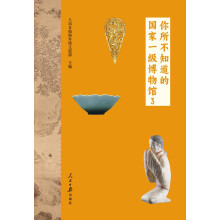绪论
两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内容在统一封建王朝背景下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墓葬这一特殊社会内容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获得较大发展,出现和形成了诸多新内容、新因素,与墓葬相关的制度、礼俗和内容等不仅是汉代社会的重要构成,也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汉代墓葬在中国古代墓葬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部设施是古代墓葬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汉代获得了多方位、飞跃性的发展,古代墓葬自身的双重世界及死者与生者的三维世界基本形成,而这也标志着古代墓葬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书即是对汉代墓葬,主要是王侯墓葬及中小型墓葬外部设施进行的综合性考古学研究。
一、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墓葬范畴和墓葬外部设施。
(一)墓葬范畴
汉代之前的墓葬,有墓外设施者多为等级较高的墓葬。
春秋时期有墓外设施的高等级墓葬已有相当数量。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区,中字形大墓即王陵及相关墓葬的陵园相对独立,且王陵上基本都有祭享类建筑物,如M37等。浙江印山越王陵使用了隍壕等设施。
战国时期有墓外设施的高等级墓葬更多,墓外设施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和多样。山西新绛柳泉战国早期晋君墓地中,已发掘的M301、M302、M303,每组上均有连为一体的夯筑封土,在第2组大墓附近采集到板瓦、筒瓦等a。河南新郑的韩国国君墓葬中,许岗墓葬区M3墓冢上的废墟堆积中发现不少战国时期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材料,当时墓上应有建筑;胡庄墓地M2封土上发现保存较好的墓上建筑,由散水、壁洞、柱石和部分屋顶瓦砾层等组成,其西侧还发现有拐角形墓旁建筑。辉县固围村魏王墓上发现“享堂”或“寝”类建筑,有散水、柱础、台基等,出土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河北地区已发现的三组中山王陵墓均有相关陵墓建筑,基本位于封土之上,M6、M7的封土顶部原都有堂类建筑;城外墓区1组的陵墓建筑保存相对较好,封土顶部保留有堂、回廊等建筑基址,存有墙壁、壁柱洞、地面、卵石散水、檐柱础及板瓦、筒瓦、瓦当、瓦钉、脊饰、砖等,封土前面平台最下一级底边的中部有瓦片堆积,说明这里可能是门阙所在,而王后墓上也有类似于“王堂”的建筑基址,说明王墓与后墓上的建筑是分置的,即每墓一堂。邯郸赵王陵中一些墓葬的封土上有相关建筑,每座陵台的东部还有既宽又长的道路,可能和祭祀或其他行为有关。湖北荆卅熊家冢M1的某些祭祀坑上或附近发现有柱洞遗存,可能是墓地的附属建筑。一些墓葬的墓外建筑已位于墓侧,陕西咸阳附近的秦惠文王“公陵”及王后陵,有陵园,陵园西侧有几处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可能属于寝或相关设施。
秦始皇陵继承前代的制度和做法,封土西侧有平面近方形,由主殿、侧殿、回廊、门道几部分组成的正殿及由若干单体建筑组合成的院落式附属建筑,并有食官建筑及园寺吏舍建筑等。
与汉代之前明显不同,两汉时期有外部设施墓葬的范畴明显扩大。除帝王陵墓、列侯贵族及相关墓葬拥有多种形式、不同类型、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墓外设施外,较多的中小型墓葬也有不同形式、数量不等,而且具有相应时代、地域和发展特征的墓外设施。
两汉帝陵外部设施众多,且存在相应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出汉代陵寝制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及其内容、组成、内涵等,帝陵是两汉政治、精神、文化的象征物和载体之一。关于两汉帝陵的外部设施,一方面考虑到相关文献与考古资料较为丰富,所需研究的内容多而庞杂,而本书篇幅有限;另一方面,帝陵具有特殊性,外部设施内容多样。目前,考古工作者对两汉帝陵的外部设施进行了诸多工作,相关资料得到不断充实和丰富,作为汉代陵寝制度研究的重点,已有较多学者从多个方面、不同角度对两汉帝陵的外部设施、陵寝制度等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鉴于以上两点,本书对两汉帝陵的外部设施不做专门研究分析,但在相关研究中会有所涉及。
汉代王侯墓葬与中小型墓葬数量大,墓外设施数量多,种类丰富,加之较多等级较高的王侯墓葬在制同中央的影响下,体现出较多与帝陵相近或相似的内容,与两汉帝陵外部设施的发展完善相对应,汉代王侯墓葬与中小型墓葬的墓外设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汉代墓葬外部设施相应的发展及其内容、内涵等。目前,关于汉代王侯墓葬及中小型墓葬外部设施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专题或综合性研究极少或不见,本书将研究所涉及的墓葬范畴定为汉代的王侯墓葬及中小型墓葬,主要包括汉代诸侯王与王后及其相关墓葬、汉代列侯及其夫人等的墓葬、各类中型和小型墓葬,相关研究即针对这些类型墓葬的外部设施展开。开展汉代王侯墓葬及中小型墓葬外部设施的研究,借鉴关于两汉帝陵外部设施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对汉代墓葬、墓葬的外部设施、丧葬制度与礼俗、相关丧葬内容等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全面、综合的认识。
(二)墓葬外部设施
墓葬外部设施,可简称为墓外设施,是墓葬之外与墓葬有关的设施。汉代,墓葬封土已全面普及,因此就本研究来讲,墓外设施基本是指封土之外的设施及封土堆筑后打破或叠压封土而形成的相关设施。
除陪葬墓、陪葬坑外,墓外的相关建筑则是衡量墓外设施发展的重要因素。汉代是墓葬外部设施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汉代之前,墓外设施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墓外建筑为例,最早可能位于墓顶或墓上,后又移至墓侧,体现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杨宽先生曾言,秦汉以后的陵寝制度,当即起源于先秦的墓上建筑。关于墓外建筑出现的年代,杨鸿勋先生认为,陵墓上建享堂很可能是奴隶制初期就已有了的,估计西周统治者的陵墓上有过享堂,不过至今尚未发现确切的实例。杨宽先生认为安阳大司空及妇好墓等商代墓葬墓上的遗迹为墓上建筑,指出商代墓地已有建筑出现。也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西周没有墓上建筑,按照常理,商代也不会有墓上建筑。
春秋中、晚期,高等级墓葬的陵园逐渐呈现出独立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墓外建筑的出现和发展。上文所举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区、浙江印山越王陵等墓葬的外部建筑出现,即用于祭祀和保护墓葬。
战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的陵园更为独立,封土墓发展,墓外建筑得到较多使用,建筑规模扩大,设施考究,更加适应于高层统治者的需求,如韩国国君墓葬中的许岗墓葬区M3、辉县固围村魏王墓及河北平山中山王陵等。墓外建筑的性质与墓祭关系更为密切,进一步来讲,这些建筑应是秦汉时期寝类墓外建筑的早期形态。蔡邕言:“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但从现有资料看,战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墓外建筑经历了由墓上移至墓侧的发展过程,这与封土的规模扩大,陵园的独立,统治者祭祀需要的扩展等有较大关系,而这也表明陵园设施的逐步规范化。有些战国王侯墓,墓上建筑与墓侧建筑共存的特征已较明确,如一些赵王陵,封土上有建筑,陵台东部还有道路;新郑胡庄墓地M2韩国国君墓,封土上有墓上建筑,墓葬西侧还有拐角形墓旁建筑;秦东陵陵区4座陵园中大型墓葬的墓外建筑都位于墓侧。以上说明,最迟至战国晚期,王陵的墓外建筑已基本移至墓侧,且有一些具备了“寝”的功能。
先秦王墓及秦始皇陵均为高等级墓葬,汉代之前等级稍低或较低的墓葬还极少有相关墓外设施内容被发现和发掘。随着汉朝的建立及其统治的日渐巩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与墓葬有关的外部设施得到较大发展,对应的墓葬等级趋于多样,分布地域渐广,设施内容和种类趋于丰富,一些新的设施开始出现。西汉晚期开始,尤其是东汉时期,墓外设施的使用得到普及,一些旧式或与时代不相适应的设施渐被摒弃,较多新型设施涌现并得到推广,特别是中小型墓葬,与墓祭、墓葬修建和守护等有关的设施十分普遍。就汉代墓葬的外部设施来讲,既不似汉代之前多服务于等级较高的墓葬,也不像先秦时期一些墓葬的设施仅位于墓上,而是较为普及,较多等级人员的墓葬皆有使用,墓上虽有相关设施打破或叠压封土,但更多的是位于墓葬旁侧或附近,甚至在墓区之内或墓地之中,构成了汉代墓葬的重要内容。
二、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
目前,与汉代王侯墓葬及中小型墓葬外部设施有关的考古资料日渐丰富,而与之有关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为全面认识汉代王侯墓葬及中小型墓葬外部设施提供了重要资料和参考。
(一)考古发现
两汉帝陵墓外设施丰富多样,而与两汉帝陵有关的考古工作很多与墓葬外部设施有关,而且成果丰硕。与帝陵外部设施的考古工作相比,汉代王侯墓葬与中小型墓葬的墓外设施多与墓葬自身的考古发掘有关,其中很多是在对墓穴进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开展,当然也有一些是先期调查、勘探或发掘,或是墓葬发掘后,对其墓外设施再进行相关考古工作。因此,汉代王侯墓葬与中小型墓葬外部设施的考古资料公布较为零散,有些仅在公布的墓葬考古资料中有所提及,有的单独公布,少量有考古报告出版,而有些考古发现不仅零散而且不具备连续性,很多还是在配合基本建设中有所发现,加之有些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或难以形成一篇简报等原因,并未能得到公布。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发展,考古工作者对于墓葬外设施的重视程度得到极大提高,很多汉代墓葬的外部设施得以公布或发表,这也使得相关研究成为可能。
需作说明的是,本书的**至五章将就不同等级墓葬的外部设施或不同类别的外部设施进行具体论述,本部分仅作概述。
1.西汉诸侯王墓葬的外部设施
截至目前,已发现和发掘的西汉诸侯墓大致为46处96座,较多西汉诸侯王墓葬有与墓外设施相关的内容公布。就西汉诸侯王墓葬的外部设施来讲,相关资料并不统一,内容也不尽相同。
有的发现有园邑遗存,有的诸侯王墓外有陵园、祠庙、寝园等遗迹,相当数量的西汉诸侯王墓外有陪葬坑、陪葬墓,而就西汉诸侯王墓来讲,异坟异穴合葬墓较为常见。除上述内容外,有的西汉诸侯王墓外还发现有园寺吏舍、道路、水井、防排水设施、手工业作坊,个别墓葬还有地标石。总体
展开